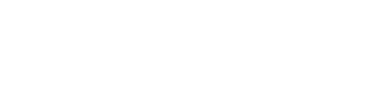【通訊】新人發聲/安勤之
2020-05-18
文/安勤之(交通大學百川學士學位學程教學教師)
大家好,我是安勤之,曾經研究「四物靈芝牛樟芝」,是物質文化、科技與社會研究以及社會學的學徒。謝謝學會在此讓我發聲。對我而言,社會學是什麼,始終是個「問題」,但我更喜歡的說法是「提問」。我感覺我的人生充滿各種問題,我自己就是個「問題」,但社會學讓我學會要勇敢「提問」,而不僅僅把自己當成問題。因而,「新人」所指為何?「發聲」的條件是什麼?我想先從自己的經歷談起。
我在台大社會系讀博士班,以中藥為研究主題。我的同學們很優秀,不過有些朋友後來未完成學業,不論是基於生涯抉擇或是遭遇制度困境,他們的選擇在當時時常出現在我腦海裡,我曾想要中輟──因而參加過社會行政高考,不過成績超差,自嘲自己天生不喜歡標準答案。因緣際會,遇到哥哥的朋友從事靈芝傳銷,我投入研究,進入直銷會場待了九個月,瞭解傳銷人員如何培養新血,我透過這些經驗,反身思考自己學習社會學的歷程。在台大時期曾參與了兩個重要的會議,一個是2012年在中研院舉辦的國際社會學會第11屆博士生工作坊,活動為期一週,結識了迄今仍維持友誼的好友;另一個則是教育部舉辦的跨國學術競爭力菁英班,活動為期為一個月,則是認識了職涯上的貴人。後來更申請到科技部與中研院的博士候選人獎助計畫,在這些條件下,加上師長友人在學業、生活與情感上的支持,讓我得以順利畢業,完成了一本探討不同社會團體如何針對靈芝爭辯其療效價值的著作──即我的博士論文《救命仙草、健康食品或生技靈藥?靈芝的科學、巿場與療效政治》。這個時候,我不是新人,也無從發聲,只是被鼓勵繼續努力。惟一的例外是,當我的論文獲得社會學年會的博士論文佳作獎時,我有了大約一到兩分鐘的機會「發聲」,我希望在場的師長多多關注在校的博士生,協助他們克服各種撞牆與卡關。效果如何,我不清楚,但如果重來一次,我還是會再說一次。我相信我的環境資源已相對優渥,但如果連我都常遇到撞牆期,那麼同行一定也會遇到,我相信這是結構性的問題。或許關鍵在於,臺灣的博士生被認為是「學生」,有著科層體系下的從屬位置,屬於產業後備軍的一環,還不具備有獨立的姓與名,不被視為學術「同行」,簡言之,不是社會學界的「新人」。他們連新人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候補選手,若是人脈或出身較佳,相對來說獲得師長熟識的機會也會較高一點,成為值得期待的「新秀」。
即使是到了「博士後」階段,似乎也難逃「後備軍」條件,但顯然已經比較接近暖身區,但反而在這樣的暖身區,對於所謂的「落選」的感受變得更深。各種聘任相關的都巿傳說流竄,誰是誰的弟子、親屬,又或者誰是內定、誰是資深老師、誰跟誰關係良好,又或者傳說只要好好寫論文,就會有機會,但實際上是人人似乎有機會,但個個沒把握的狀態。在這樣的氣氛下,我作了一個調查,探討臺灣畢業土博的去從,我的結論仍是如何幫助臺灣的博士班學生,面對「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的時代」能夠有更完備的訓練,更堅強的心志,面對這不確定的時代,不致於鬱鬱寡歡,抑鬱而終,而能夠展現出面對時代困境的學人氣魄。博士後階段,似乎已經是「準新人」,但未來怎麼發展,沒有人說得準,或許師長早逝,或者懷才不遇,或者且戰且走,或者另闢新局,展現能動性。於我而言,學長姐的經歷是警惕也是借鏡。
離職後的我,選擇探問政府怎麼幫助我們這群失業博士。於是,我去了就業服務站,通過失業補助審核,成為失業人口,獲得勞保額度六成的補助,預備度過這半年。後來師長推薦一年博後研究「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對於學員影響」的機會,我藉此瞭解了學員的不同人生際遇與他們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評價。在這樣的緩衝之下,繼續求職,參加師長們舉辦的讀書會,而熱心的師長鼓勵我去應徵交大百川學士學位學程,而我榮幸獲得肯定,得以有了教職身分。我現在正式成為所謂「新人」,可以獲得學會提供的一個「發聲」機會,在學會的正式刊物上留下我的名字。但是我的敏感度與脆弱卻提醒著我,那些曾經一起學習,一起參加研討會,一起應徵同間學校的同儕們,他們還在等待發聲的機會,他們還在暖身區,又或著回到了冷板凳,或者退場,即使西進中國,也希望保持低調,亦或以暖身為名,機遇為念,長期滯留在「學術非穩定工作」狀態中。想到這裡,我似乎無法發聲了。「新人」之名不該屬於我,而應該屬於一群人,他們是專案教師、他們是兼職教師、他們是博士後,他們是博士生。他們才應該「發聲」,讓無法發聲的人發聲,這才是社會學,不是嗎?
這幾年的博士後生涯,我反覆閱讀的一本著作,就是布爾廸厄的《自我分析綱要》。他總是說,理解,就是理解一個場。他從結構位置的軌跡來思考他自己何以成為學術人。對我而言,「新人發聲」提供了一個反省個人過往軌跡的機會,家庭條件、階級位置、社會軌跡,同儕社群都影響了我的養成過程,我恰巧佔據了那些較為優勢的位置,並且善加利用了這些位置,我很感激師長們的協助。韋伯雖然在〈學術作為志業〉裡提到,一個人找得到學術工作是機運,像他的優秀學生就沒找到工作,但我認為重視「志業人」與在意「德國靈魂」的韋伯,用「機遇」這樣的話語,無疑是隱晦之語。優秀的人才值得更好的「機遇」、值得更好的「待遇」、值得更好的「遭遇」,而不僅是過渡性的勞動力,計畫性的人力資源,非穩定性的動員。如何健全社會學場域、健全大學體制、健全勞動體制、健全國家體制,同時在基礎構造層面,將具備「博士生」、「博士後」、「專案教師」、「兼職教師」身份的社會學人才庫建置明朗化,皆視其為「新人」,建立交流的平台與提供實體或虛擬的對話空間,提供實質層面或精神層面的協助與鼓勵,擴大社會學在臺灣的影響力,我想是克服「機遇隱語」,在制度上該作的偉大嘗試。
大家好,我是安勤之,曾經研究「四物靈芝牛樟芝」,是物質文化、科技與社會研究以及社會學的學徒。謝謝學會在此讓我發聲。對我而言,社會學是什麼,始終是個「問題」,但我更喜歡的說法是「提問」。我感覺我的人生充滿各種問題,我自己就是個「問題」,但社會學讓我學會要勇敢「提問」,而不僅僅把自己當成問題。因而,「新人」所指為何?「發聲」的條件是什麼?我想先從自己的經歷談起。
我在台大社會系讀博士班,以中藥為研究主題。我的同學們很優秀,不過有些朋友後來未完成學業,不論是基於生涯抉擇或是遭遇制度困境,他們的選擇在當時時常出現在我腦海裡,我曾想要中輟──因而參加過社會行政高考,不過成績超差,自嘲自己天生不喜歡標準答案。因緣際會,遇到哥哥的朋友從事靈芝傳銷,我投入研究,進入直銷會場待了九個月,瞭解傳銷人員如何培養新血,我透過這些經驗,反身思考自己學習社會學的歷程。在台大時期曾參與了兩個重要的會議,一個是2012年在中研院舉辦的國際社會學會第11屆博士生工作坊,活動為期一週,結識了迄今仍維持友誼的好友;另一個則是教育部舉辦的跨國學術競爭力菁英班,活動為期為一個月,則是認識了職涯上的貴人。後來更申請到科技部與中研院的博士候選人獎助計畫,在這些條件下,加上師長友人在學業、生活與情感上的支持,讓我得以順利畢業,完成了一本探討不同社會團體如何針對靈芝爭辯其療效價值的著作──即我的博士論文《救命仙草、健康食品或生技靈藥?靈芝的科學、巿場與療效政治》。這個時候,我不是新人,也無從發聲,只是被鼓勵繼續努力。惟一的例外是,當我的論文獲得社會學年會的博士論文佳作獎時,我有了大約一到兩分鐘的機會「發聲」,我希望在場的師長多多關注在校的博士生,協助他們克服各種撞牆與卡關。效果如何,我不清楚,但如果重來一次,我還是會再說一次。我相信我的環境資源已相對優渥,但如果連我都常遇到撞牆期,那麼同行一定也會遇到,我相信這是結構性的問題。或許關鍵在於,臺灣的博士生被認為是「學生」,有著科層體系下的從屬位置,屬於產業後備軍的一環,還不具備有獨立的姓與名,不被視為學術「同行」,簡言之,不是社會學界的「新人」。他們連新人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候補選手,若是人脈或出身較佳,相對來說獲得師長熟識的機會也會較高一點,成為值得期待的「新秀」。
即使是到了「博士後」階段,似乎也難逃「後備軍」條件,但顯然已經比較接近暖身區,但反而在這樣的暖身區,對於所謂的「落選」的感受變得更深。各種聘任相關的都巿傳說流竄,誰是誰的弟子、親屬,又或者誰是內定、誰是資深老師、誰跟誰關係良好,又或者傳說只要好好寫論文,就會有機會,但實際上是人人似乎有機會,但個個沒把握的狀態。在這樣的氣氛下,我作了一個調查,探討臺灣畢業土博的去從,我的結論仍是如何幫助臺灣的博士班學生,面對「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的時代」能夠有更完備的訓練,更堅強的心志,面對這不確定的時代,不致於鬱鬱寡歡,抑鬱而終,而能夠展現出面對時代困境的學人氣魄。博士後階段,似乎已經是「準新人」,但未來怎麼發展,沒有人說得準,或許師長早逝,或者懷才不遇,或者且戰且走,或者另闢新局,展現能動性。於我而言,學長姐的經歷是警惕也是借鏡。
離職後的我,選擇探問政府怎麼幫助我們這群失業博士。於是,我去了就業服務站,通過失業補助審核,成為失業人口,獲得勞保額度六成的補助,預備度過這半年。後來師長推薦一年博後研究「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對於學員影響」的機會,我藉此瞭解了學員的不同人生際遇與他們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評價。在這樣的緩衝之下,繼續求職,參加師長們舉辦的讀書會,而熱心的師長鼓勵我去應徵交大百川學士學位學程,而我榮幸獲得肯定,得以有了教職身分。我現在正式成為所謂「新人」,可以獲得學會提供的一個「發聲」機會,在學會的正式刊物上留下我的名字。但是我的敏感度與脆弱卻提醒著我,那些曾經一起學習,一起參加研討會,一起應徵同間學校的同儕們,他們還在等待發聲的機會,他們還在暖身區,又或著回到了冷板凳,或者退場,即使西進中國,也希望保持低調,亦或以暖身為名,機遇為念,長期滯留在「學術非穩定工作」狀態中。想到這裡,我似乎無法發聲了。「新人」之名不該屬於我,而應該屬於一群人,他們是專案教師、他們是兼職教師、他們是博士後,他們是博士生。他們才應該「發聲」,讓無法發聲的人發聲,這才是社會學,不是嗎?
這幾年的博士後生涯,我反覆閱讀的一本著作,就是布爾廸厄的《自我分析綱要》。他總是說,理解,就是理解一個場。他從結構位置的軌跡來思考他自己何以成為學術人。對我而言,「新人發聲」提供了一個反省個人過往軌跡的機會,家庭條件、階級位置、社會軌跡,同儕社群都影響了我的養成過程,我恰巧佔據了那些較為優勢的位置,並且善加利用了這些位置,我很感激師長們的協助。韋伯雖然在〈學術作為志業〉裡提到,一個人找得到學術工作是機運,像他的優秀學生就沒找到工作,但我認為重視「志業人」與在意「德國靈魂」的韋伯,用「機遇」這樣的話語,無疑是隱晦之語。優秀的人才值得更好的「機遇」、值得更好的「待遇」、值得更好的「遭遇」,而不僅是過渡性的勞動力,計畫性的人力資源,非穩定性的動員。如何健全社會學場域、健全大學體制、健全勞動體制、健全國家體制,同時在基礎構造層面,將具備「博士生」、「博士後」、「專案教師」、「兼職教師」身份的社會學人才庫建置明朗化,皆視其為「新人」,建立交流的平台與提供實體或虛擬的對話空間,提供實質層面或精神層面的協助與鼓勵,擴大社會學在臺灣的影響力,我想是克服「機遇隱語」,在制度上該作的偉大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