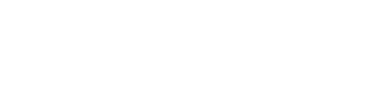【通訊】新人發聲 / 舒奎翰
2024-02-05

舒奎翰 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大家好,我是舒奎翰,於2022年到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開始任職。承蒙王秘書長的邀稿,小弟就在此分享一些自己的學術歷程。
嚴格來說,我的學術生涯不算精彩,因為唸書的時間很長,但是卻只有很少的學術產出,這多少跟自己的個性有點關係。我大學以上的學歷分別是東海政治系學士,東海社會系碩士,交大社文所博士,在三個不同的階段分別念了三個不同的科系,所謂的跨領域大概在我身上實踐了不少。但我大學階段的學習對我後來的研究有很深遠的影響,這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個是剛好碰到國內外政治與經濟情勢產生巨變,在國內正逢台灣開始走向民主化與本土化,在國際上則是兩德統一、蘇聯瓦解,冷戰結束。那時的社會風氣異常開放,很多事情都在嘗試與摸索,爭執與衝突不斷,但是新奇、有趣和創新的構想與嘗試也不斷出現。正在念政治系的我們,知識上身處變革的最前線,要如何整理過去的政治局勢與面對未來,是大學唸書時討論的重心。台灣民主化的相關議題牽涉很廣又很複雜,包括憲政體制、公民社會的角色、間接民主還是直接民主、政黨政治、選舉制度、政治文化變遷、比較政府與政治、現代化與民主化、去威權化(現在叫轉型政治與民主鞏固)與本土化、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等。對這些議題的接觸除了透過修課,也包括參加各種研討會(那時的研討會很精彩,吵架是常有的事),看出版的書籍、報章雜誌的報導與評論,以及同學的閒談。最後一個看似最不學術,但卻是最真實的生活經驗分享。例如省籍衝突與國家認同,同學們因為家庭背景經歷的不同,對這些議題的反應與思考答案是非常不同的。曾有本省籍的同學跟我說你作文好是因為你是外省人,本來就講國語,寫作的時候不用轉換。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所謂的語言優勢是怎麼回事(這個現在年輕人身上可能比較少見了)。又有人討論到之後結婚對象的選擇,若是有省籍上的考量,居然是擔心女性做的菜可能無法符合長輩的口味喜好因此被嫌棄。這些內容現在聽起來似乎很可笑,但會從人們腦中浮現,代表這些生活上的瑣事更可能是爭執的引爆點。這些閒談可以看出省籍問題在當時對許多人來說,不僅是政治的符碼與口號,而是真實生活中的一部份。而這些經歷對我之後一直是思考問題的起始點,也是重要的素材來源。
到碩士班轉念社會學研究所是一種機緣巧合,大學的時候就有聽學長講社會系又有哪個老師新進回國任教,講課的內容又跟政治系有哪些不同。大四的時候去修了趙剛老師開的大一社會學,上課的時候光唸他開的讀本就感到很吃驚:分量比政治系多,討論的面向也更多、更有深度。那時就起了一個念頭,要是碩士班能念社會系好像能學到更多。後來各種機緣跟好運的結合下,考取了社會系碩士班。這個過程真的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折點,這是因為,第一,當時社會系的師資在國內絕對是數一數二,除了高承恕與熊瑞梅兩位較資深的教授之外,其他多數都是剛從美國名校學成歸國,把最新的學術資訊跟頂尖大學做學問的風氣帶了回來。簡單的說,在這個時期我才真正認識到什麼叫學術以及做研究最起碼該有的基本規格與要求。第二,朱元鴻老師願意讓我擔任國科會計畫的研究助理,就這樣跟著做研究,並成為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開展之後迄今長達數十年的師生情誼,對我不論是做學問還是人生歷練都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不過我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倒是與政治無關,而是關於台灣傳統的民間信仰如何在現代化的都市地區延續。這個研究主要是要解答我自己心中一個小小的疑惑:過去的研究都預設都市化與現代化會讓傳統的宗教信仰力量減弱,但在台灣,倒是在都市看到越來越多的寺廟(與神壇),要怎麼解釋這個現象?我的研究顯示,都市化與現代化改變的不是信仰,而是宗教社群的組成方式。在現代社會,信仰的需求並未消逝,相反的在強調個體主義的時代,孤獨感增強的個人反而更會尋求宗教的慰藉。但傳統的宗教社群(例如因庄頭廟而組織起來的地方社群,或是因地方社群需求而產生的庄頭廟)確實因為傳統連帶的崩解而改變了經營與組織模式,也讓功利性較強的神壇(私廟)變得越來越多,信仰的內涵也因此日益功利化。在最近最令人不願看到的轉變則是,這些具營利性質的宮廟逐漸成為了黑道勢力插旗所在,信仰染黑在未來將會變成尾大不掉的社會議題。
碩士班畢業之後,我暫時投入職場工作,之後還是決定選擇以學術工作做為畢生的志業,因此開始攻讀博士班。不過當時朱元鴻老師已經轉任於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就這樣,跟隨著朱老師的腳步,我進入交大社文所就讀,這一唸,就是十年。
跟碩士班不同,博士班的階段是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進去的,亦即我想討論,在強調理性思考與溝通的年代,為什麼情感與情緒在現代民主政治裡扮演重要的角色?現在這樣的研究可以歸類在情感政治這一塊,而且研究者眾,但在當時還是塊處女地。然而,有個問題是顯而易見但卻必須優先克服的:在這個充滿變動又危機感四伏的年代,集體性的情感與情緒(例如恐懼、焦慮、怨恨等)是個顯而易見的現象,而且容易被操弄。這樣情感是依變相嗎?然而,情感與情緒也有其自主性,甚至有時被看成是主體性的主動展現。學界關於這部份的討論牽涉甚多又廣,加上近年來腦神經科學、心理學等領域對於情感與情緒的研究有著突破性進展,一個沒注意就越唸越多,忘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博士論文只是要證明自己有獨立研究的能力,換句話說,博士身分是進入學術界資格的起始點,只是開始,而不是結束。因此控制論文寫作的範圍是很重要的功課,在這部份沒有掌控好而導致修業年限過長,對自己的學術生涯發展並不是好事。
當然在社文所十年的時間也是經歷非常多的事情,我剛進去的時候才設立不久,具有很高的實驗性質。社文所雖然中文全名有「社會」兩個字,但在英文的名稱中可是沒有Sociology的,而是以social research取代,外界主要都是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這個title來界定這個學術單位,而很少強調社會學的部份,也算其來有自。而這期間最有趣的是和一群搞「文化研究」的人相處,尤其是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博士生,與他們談學術會有開了另外一扇窗的感覺(很有趣,真的很有趣,很生活可是又很深刻,光講一個陶藝就可以連結東西,橫貫古今,讓你之後每次吃飯面對瓷器餐具都不由得肅然起敬),而且會立刻意識到,這群人的思維模式跟讀社會學的很不一樣。另外,所上老師的開課與舉辦的演講、座談、研討會及國際學術交流等活動涉獵的範圍極廣,從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英美文學評論、藝術評論、文化人類學、哲學、美學、倫理學等,甚至還包括國際地緣政治等議題。這是很精彩的十年,但也是很辛苦的十年,但總的來說,這是值得與慶幸走過的人生。
照理說,這篇自介文章應該多說說自己的研究專長與研究興趣,但我的學術工作從畢業至今因找工作中斷許久,現在要重新找到方向尚須時日,在此不擬多談。倒是想藉此機會與各位分享一些教學經驗。從我在交大就讀開始,因為兼課的關係,所以從頂大到報考名次較為後段的大學學生都教過,很明顯意識到兩個因素對教學品質的影響。第一個是貧富差距與城鄉差距對於教育的影響日益嚴重,因為這兩者是日益擴大的。我這幾年稍微做了一些調查,發現能夠唸頂大的學生,家長身分為專業受薪階級的比例很高,這裡的專業階級是指領有「高階」專業證照的人,例如醫生、教授、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心理諮商師等等,換句話說,家庭平均年薪是百萬為基準點起跳。印象最深的是有學生父親是外交大使,從小跟著父親在歐洲生活,英語對他來說從不是問題。這些學生教起來很愉快,他們素質好,企圖心強,對世界充滿熱情與好奇心,不怕接受困難與挑戰,對自己充滿自信,對未來充滿期許。儘管在唸比較難的學理課程時(例如社會學理論)還是會有點挫折感,但往往很快能調適並掌握到學習要領,素質更好的甚至能舉一反三,有時都覺得教到學術接班人了。相對的,名次較後段的大學招募到的學生家庭背景中,經濟比較弱勢不說,家長通常也缺乏文化與教育資本,孩子遇到學習上的問題往往丟給補習班去解決。另外就是有一定比例的單親與外籍配偶的家庭,有些甚至連基礎的中文都無法清晰的表達。當然不是說頂大的學生經濟家庭背景就一定很好,而錄取排名較後段的大學的學生經濟家庭背景就一定比較弱勢,但有我遇到幾個案例顯示,就算在後段大學的學生,經濟狀況較好的家庭在學習表現上相較於同校的學生一樣有優勢,特別是在學習主動性跟吸收能力上(還有一個就是對探索世界的好奇心)。而頂大的學生,最大的差別表現在語文成績上,經濟資本較好的,往往外語能力都不差,至少不排斥或是懼怕學習(家裡從小就培養雙語環境,出國參加短期營隊是常態)。相反的,經濟條件較差的,往往外語能力的表現就沒那麼突出,也比較少顯示繼續學習外語的企圖心。如果我們預設教育的功能是能夠改變一個人階級處境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我現在真的非常懷疑這樣的預設在多大的程度上還是具有功能的。當然上述這些其實在許多相關書籍,例如藍佩嘉那本知名的『拼教養』一書都能夠看到,但看書中的描述是一回事,親身經歷總是另外一回事,有些事情,你得自己走過才能知曉箇中滋味。
第二個就是少子化。這個的議題已經好些年了,但從去年開始應該包括一些老牌的私立大學,例如文化跟淡江都開始面臨到巨大的招生壓力。其實數字會說話,再過幾年,全國的高中畢業生將連國立大學都塞不滿,也不知道屆時能存活的私校還能有多少。在這種情況下,私校只能先冀望招到學生,至於學生的素質以及是否適合念該科系等都先擱置,反正人先進來再說。少子化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導致排名越後段的大學學生的素質普遍都不盡理想,從而讓授課老師必須加大力道才能讓學生達到學習標準,這樣就壓縮了研究的能量與時間。但大學的教師嚴格來說不是教員,因為大學講堂不是一個照本宣科的地方,授課老師應該隨著自己的研究與知識的擴展不斷調整自己的授課內容,這樣才不至於落伍,學生也才能學到最新知識。但少子化讓原本應該正向循環變成了負向,而且挫折感重的不僅是授課老師,也包括學生。他們並不是不想學,是學不了。但關於這個議題,台灣這幾年好像也沒看到傑出的研究來解釋說明到底台灣社會發生了什麼事,或許這個議題真的值得大家一起努力好好研究一下,而不是理所當然的覺得就這樣了(我們真的能接受沒有孩子的未來嗎?)。
總的來說,我從念大學開始,在東海前後待了十年,在交大社文所又待了十年,前後二十餘年的時光都是學生身分,基本上不是新人,是老生了。我經歷了台灣搞理論最輝煌的年代,連搞政治運動都要搞讀書會講理論。但這幾年很明顯不那麼講理論了,而是重視實務上的經驗與分享,教學的重心也從講授學理慢慢轉向實作與共同參與,這也算另一種風水輪流轉吧。但必須要說,我懷念那個理論狂飆的年代,那時候唸書真的很過癮。以上就是一點心得分享,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