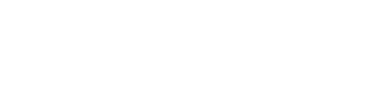楊又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移動,作為生存策略
現在回頭看,人生至今各個重要抉擇,從學習領域的多次轉換到從事學術工作,都是在回應對自己和對社會的各種困惑。小時候看電視劇,劇情多半充斥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常規,但我沒有因此看著看著就變成異性戀;取而代之的,是對於自己長大後必須跟著這個社會腳本和異性共組家庭的恐懼。年紀稍長後,我發現遠離家鄉、搬到國外定居是擺脫這個異性戀常規腳本的可能解方。當時,有限的媒體報導再現了歐美都會區的同志街區,描繪當地性少數群體如何集結與構建出一個包容開放、令人嚮往的生活樣態。於是我立定志向當外交官,期待藉工作之便逃離台灣。然而,等進入大學主修國際關係時,社會風氣已出現微妙變化。在眾多同運前輩和民間組織長期努力地奔走倡議下,在台灣以同志身份過生活和享有其他公民權利,成為可以期待的未來。換句話說,離開台灣已無必要。與此同時,我在歐陸交換學生的經驗,特別是在各種實體和虛擬同志空間頻繁遭逢諸如「No Asian」這類歧視性話語,除了粉碎我對於在西方國家定居生活的憧憬,也讓我進一步意識到LGBTQ+社群內沿著各種身份認同所衍生的多重排他性。這一連串個人和社會結構的互動,除了持續影響我後來的遷徙軌跡,也引發我對於性/別跟跨國移動研究興趣,還有對於性少數數群體內部交織性壓迫的關注:性/別如何形塑人們各種短期或長程的移動行為?同志社群內部為何有無止盡排擠他者的劃線實作。
移動,作為研究主題
循著上述研究關懷,我的博論聚焦台灣男同志旅遊曼谷的觀光實踐,探討曼谷這座城市為何被男同志們視為構築歸屬感的「娘家」;思索他們為何在曼谷旅行的時空中頻繁參與各種平日不敢或不會進行的逾矩性互動?也剖析這些反覆的跨國移動對於男同志個體的認同建構具有什麼意義;以及,折射出台灣與東亞地緣政治哪些動態發展的社會現況?透過跟著六十五位台灣男同志在曼谷旅遊的移動式參與觀察,還有前後針對六十二位具曼谷觀光經驗之台灣男同志的深度訪談,我發現國家間不均等的經濟發展造就泰國社會中慾望「東亞人種」的集體情慾偏好,使得多數受訪者在曼谷的情慾市場裡享受國族紅利,而體驗到個人性魅力提升與當地人熱情提供性款待的特權,於是產生「回娘家」的情感結構。這種主觀感受揉雜了泰國性產業發達和出國匿名性的客觀環境,使得曼谷成為一個具高度「閾限性」(liminality)且「哈東亞」的性場域,讓台灣男同志可以超脫日常生活中「得體」(respectful)性道德政治和單一審美觀對於他們發展情愛與肉體親密關係的限制甚至是劃界排除;另方面,他們也運用各種展演策略,將這些親密經驗轉化為回台灣後融入主流男同志社群的社會資本跟性資本,顯示跨國移動的觀光實踐作為讓受訪者「登大人」成為「正常」男同志之過渡儀式的性認同建構意涵。
移動,作為可能解答
延續性/別與移動的研究主軸,下個階段我將視角拓展到LGBTQ +群體的跨國遷徙活動,並加入「勞動」這個研究面向,嘗試探討酷兒移民在異國的勞動身份如何賦予或是剝奪他們在工作場所中的性認同表達自由以及在私生活裡的親密關係發展管道;同時,也剖析性少數身份對於酷兒移民的跨國就業帶來哪些機會與限制。這個勞動與性/別所交織的多元遷徙圖像,除了鑲嵌於遷徙東道國的移民法規、勞動市場、社會性別友善風氣等國內結構條件上,也隨著酷兒移民本身多重交織的各種身份而不斷變動,尤其是國族。諸多研究已論證國族身份在移民的工作與親密等生活層面上的價值與意義,而這往往又連結到更為複雜的地緣政治角力與全球不平等架構等國際背景因素。但是,在這樣的遷徙敘事下,酷兒移民與結構對抗協商的能動性尚未獲得足夠的關注與討論。因此,我嘗試透過遷徙國外的台灣男同志、中國男同志以及移居台灣的外籍男同志這三組在原生國社會性別友善程度、國族身份象徵意義上截然不同的群體為研究對象,援引場域理論的「資本轉換」概念,企圖理解他們如何在國內與國際的物質性和論述性(discursive)條件所形構的遷徙結構中,運用個人多重交織的各種身份在勞動市場與親密生活等不同場域裡動態地協商在異國安身立命的「酷兒宜居性」,展現移民與地方之間流變可塑的人地關係。藉由這個研究計畫。我期待能呈現LGBTQ+族群的跨國移動樣態和真實生命經驗,也希冀進一步耙梳理解這個邊緣群體在各種交錯場域間切換身份的生存策略,繼續為跟我一樣對於自我和對於社會充滿困惑的人,提出可能的解答。